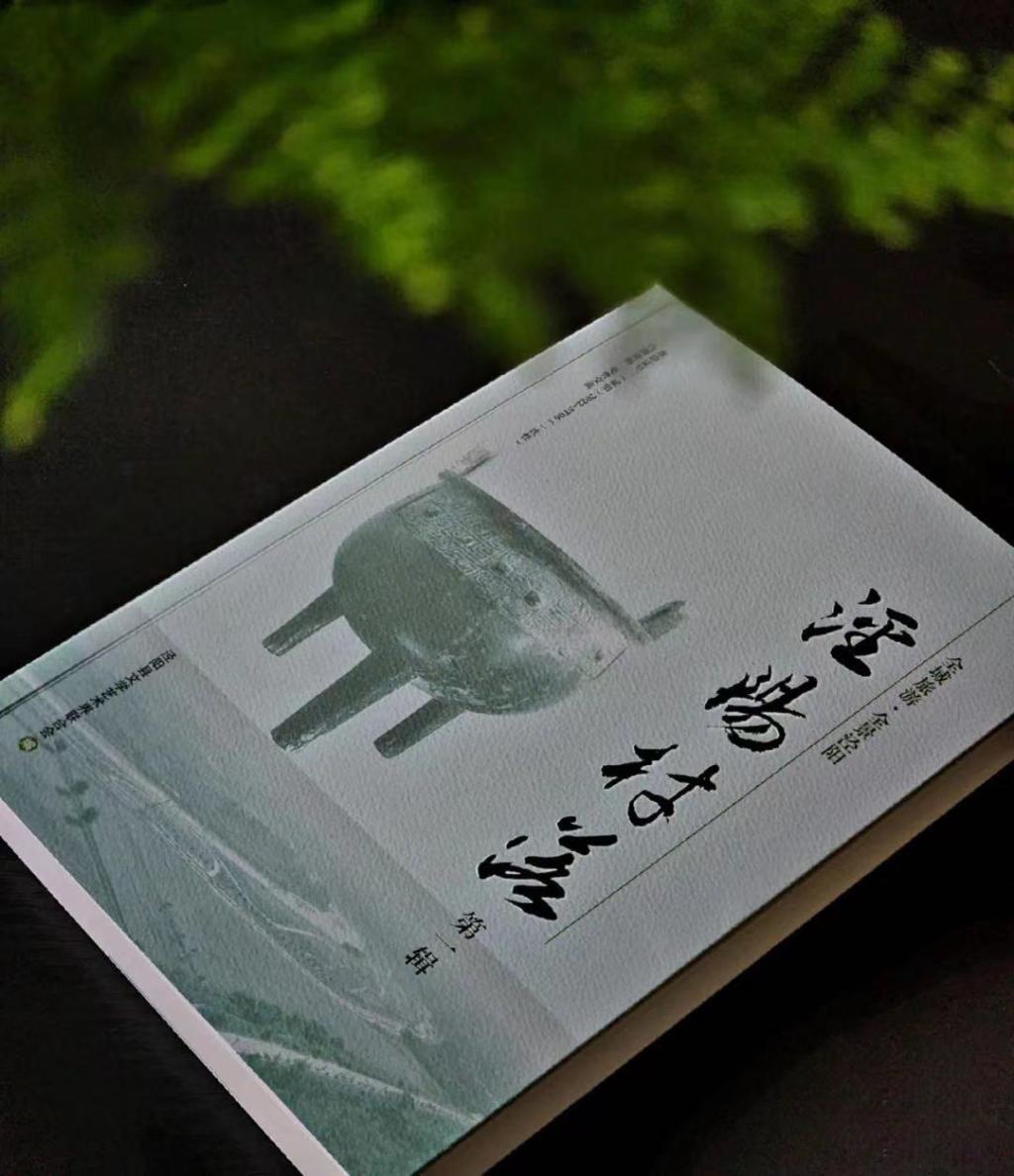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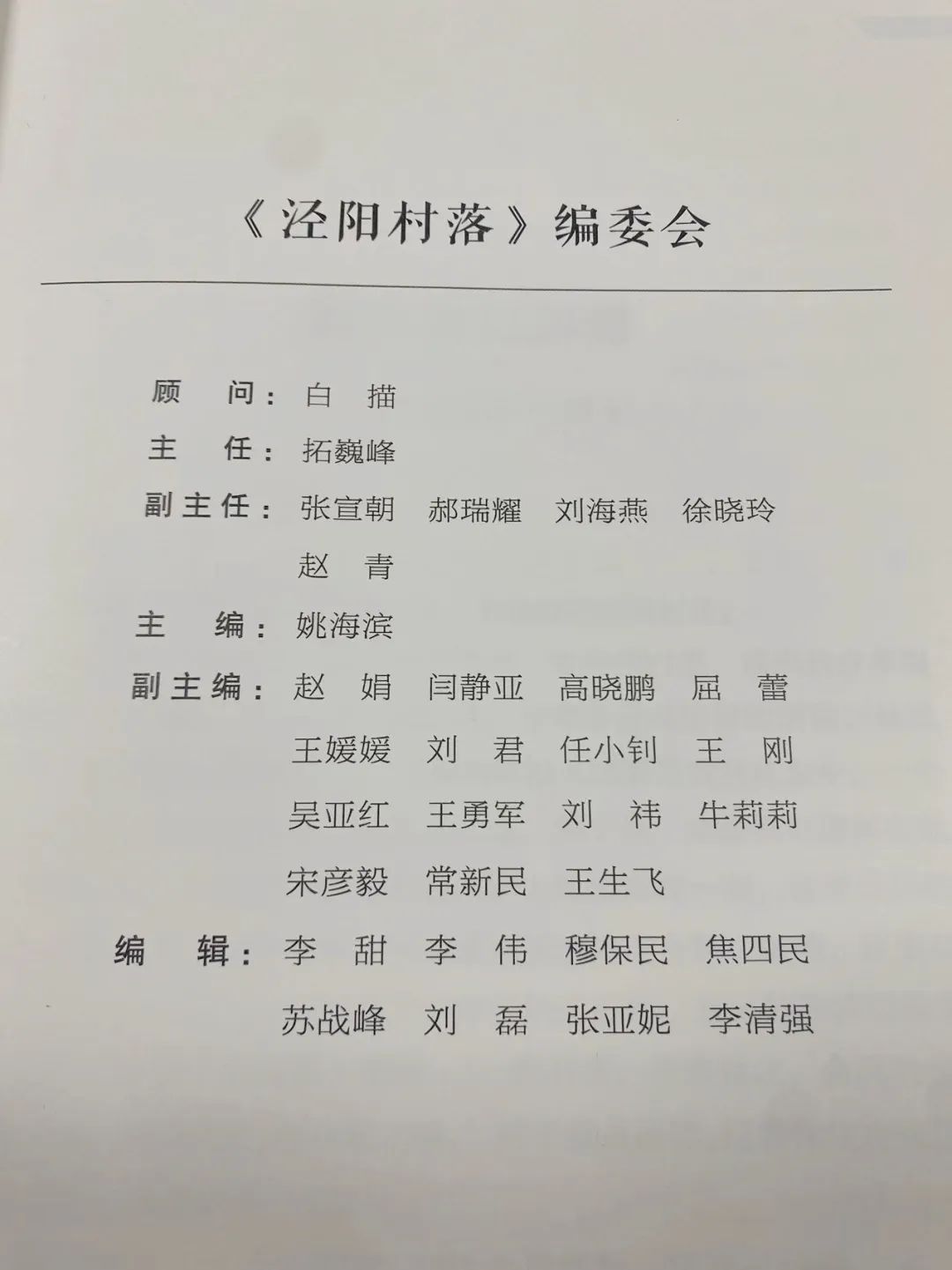
角雒村���,是一段抹不去的兒時記憶
王 楠
請聽聽一位光榮在黨五十年的老黨員, 在村黨支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發(fā)自肺腑的即席發(fā)言吧:“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,咱們國家在世界上���,現(xiàn)在是前所未有的強大�!像我們這些七八十歲的老人���,眼看著國家?guī)资陙淼陌l(fā)展����,可以說是過去現(xiàn)在兩重天!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�����,咱老百姓的衣��、食����、住、行���、用�,是前所未有的好�!現(xiàn)在人們穿衣服,講的是款式�����,講的是牌子���,講的是質量�,講的是休閑��,啥好看穿啥、啥時興穿啥�!現(xiàn)在人吃�����,講的是營養(yǎng)��,追求的是養(yǎng)生���,講的是健康環(huán)保����!現(xiàn)在人的住房�����,全都是水泥磚混平房�、樓房,出行不是汽車就是電動車��,家用電器應有盡有�����,生活、生產實現(xiàn)了電氣化����、機械化!水泥路四通八達�,就連生活垃圾都有專門的人上門拉走了,大街小巷環(huán)境衛(wèi)生整潔��。這些變化����,且不說解放前,就是改革開放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�����!我的深切感受是�,現(xiàn)在的農村比城市都好!這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功勞��!現(xiàn)在是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了�����,我們還有幸趕上了好社會��,一句話:聽黨話跟黨走,要相信�����,咱老百姓日子會越來越好的����!”
老人真誠激昂的幾句話�����,贏得了臺下一片熱烈掌聲���。這掌聲���,是對新生活的喝彩,是對黨恩的感謝����,是對改革開放的贊美!
家鄉(xiāng)的昨天啥模樣�?
兒時的記憶是抹不去的,更多的是快樂無窮�����。請跟我穿越哦……
難忘之一:一處大院落
“自古咸銅一條路”。寬約八米的石子路穿村而過�����,把我村分成東西兩半�。全村大約一百二十戶人家,大部分戶都在路西��,東邊十來戶人家����,都是東隊的人。西邊有三條不到百米的村街���,把整個村子分成東隊���、西隊和北隊三個生產隊。路東有不到七八戶人家�����,誰不挨誰,也沒有完整的院墻��,各家的大門朝向東西南北都有��,其中有一兩戶就沒有正兒八經的大門���。莊前屋后雜七雜八����、參差不齊的各種樹就那么默默長著�,最多是老榆樹��。每年春天�,榆錢飯成了度春荒的一道主打。全村清一色的土房子���,除了三五家有錢戶的土房的地基是用磚砌成��,也就七八層磚���。磚砌成的窄而高的門樓尤為顯眼,一看就是富家人�����。村里的男女老少幾乎沒有不穿補丁衣服的,無非就是那幾戶有錢人的補丁顏色比較一致罷了���。一天兩頓飯的日子一年到頭���,咸菜、酸菜是家家戶戶的長跑菜����。特別是到了冬天,數九寒天幾乎看不到人��,只有到了兩頓飯的時候���,各家各戶的煙囪陸陸續(xù)續(xù)冒出青煙����,整個村子頓時活躍起來��。我的鄰居五爺手里端著的一老碗稠包谷糝子飯�����,碗的邊上頂著的兩攪(兩成的麥面和八成的玉米面)炒面,他用筷子抄起一口玉米糝在炒面上就那么一蘸���,隨即送進嘴里���,咕咕嚕嚕兩三下就進了肚子。有時候我能眼巴巴看著他把一碗飯吃完�,一老一小誰也不說話。現(xiàn)在想起來���,也許除了咸菜再沒有啥菜吃了���,就用炒面下飯的吧,當時自己是多想知道五爺爺的那一碗苞谷糝飯有多好吃呀����!公路上大大小小的石頭����,往往墊得腳生疼生疼的,也很費鞋底子���,幾乎每雙鞋底子的腳后跟被磨出個圓窟窿����。村子里的路不怎么平整,到處坑坑洼洼的�����。有一個患過小兒麻痹癥跛腳的爺爺走起路來����,左右晃得似乎隨時能倒地,可我一次都沒有看見他倒地的樣子�。
難忘之二:三夏大忙,驟雨搶場

▲焦四民/畫
“三夏大忙��,龍口奪食�,繡女都得下床”?���!爱敭敭敗敭敭敗币魂図憦厝宓拟徛曂蝗豁憘€不停,頓時黑壓壓的烏云���,夾雜著轟隆閃電從西北滾滾而來�,眼看著一場大白雨來了�����!隨著急促的鈴聲,凡是能出工的男女勞力����,放下手里的活,拿上杈爭先恐后往場畔跑��。圍著滿場攤曬的半米高的麥秸稈���,成一個圓形排開��,大部分人在前邊一杈接一杈挑起麥秸稈朝著中間捲���,后面的人賣力地用大掃帚邊掃邊用木锨把麥籽攢起來,堆成一堆�。人多力量大,足有四五畝地大的一場連稈帶籽麥子��,堆成了七八個如小山似麥垛子���,等雨過后,可又趕緊攤開來曬�,怕垛子發(fā)燒�,不然的話就燒壞了麥籽��。攢起來的麥籽��,剛剛用大帆布把麥籽蓋上�,豆大的雨點就不由分說地砸了下來!搶場的人們相互照應著呼呼呼地又各奔東西回家了���。夏收接近尾聲�,一車車裝滿“公糧”的大馬車���,魚貫而行進了三渠糧站���。一路上,車把式把鞭子甩得“啪啪啪”�����,清脆而悠遠����,真像電影《青松嶺》里的鏡頭。這其中�����,就有我的老姨夫周宗義,一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里標本式的農民?,F(xiàn)在想想,社員們搶的是“自己的勞動果實���,搶的是愛國糧食”�,這股子鮮活的勁頭是集體主義力量的生動體現(xiàn)���!
難忘之三:分 菜
還有一件令我興高采烈的事兒��,就是提上個碎籠籠�,到隊里的菜園子領菜�����?���?磁?:一群群小娃們呼朋引伴,一個個活蹦亂跳的你追我趕���,大人們胳膊挎著個籠有說有笑��,急急忙忙直奔村北的菜園子���。大概有一里半路吧,盡管疙里疙瘩的路�,卻毫不影響人們的速度,長期練出來的哦����。分菜的場面可謂熱鬧啦:菜是按人頭分的,最多的是九口人�����,只有寇�、安兩戶,最少的是一口人����,也只有一戶,就是我婆�����。菜堆堆分門別類一字型排開�,邊上豎立著一個紙板牌牌���,上面用大字筆寫著幾人幾人字樣。碎娃跟在大人后邊�,在一堆堆大大小小的菜堆子中間,轉來轉去���、挑挑揀揀����,一會看看這個堆堆大�、轉過身可說那個堆堆大……呵呵,五十六戶的菜�,是老劉爺爺一秤一秤稱出來的,哪可能大了小了�����、多了少了呢�����?都是人們的心理作用�����。遇到分西紅柿,你看大人把個菜籠看得緊的���,就是舍不得給娃吃個西紅柿、黃瓜�,還哄著說“回去給你做洋柿子雞蛋湯泡饃……”每次分菜,我婆都是讓我去領�,也總是那么少 :三兩個辣子、一兩個西紅柿�����、一個茄子�����、一個白菜�����、一兩個紅白蘿卜����、一半根黃瓜、一小把韭菜或豇豆。如分的是西紅柿�、黃瓜,有時候不到家我就給吃了����,我婆從不罵我,還是一句湖北話“小娃子哦”���。盡管如此之少���,還是老劉爺爺照顧得呢,不然的話還會更少��。也因此緣故��,多年后���,每年清明節(jié)上祖墳��,我總是給老劉爺爺墳頭放些紙錢��,他老人家唯一的兒子早多年前也病故了�����。
我印象中�����,一年四季只有收麥子的季節(jié)和砍玉米稈季節(jié)里�����,才有分菜的時候����,菜的種類也不多�。那個時候把糧食種植抓得非常緊,一個生產隊能有個幾畝地菜園子就已經很不錯了��。
哦�,差點忘了,還有個集體豬圈����,不到十頭豬的規(guī)模,屬于自繁自養(yǎng)��。聽大人們說�����,養(yǎng)幾頭豬主要是為了豬糞,給菜園子提供肥料的�。負責養(yǎng)豬的是肖爺爺,他能給豬做一些簡單的防疫���,還是老貧協(xié)����,是不是黨員我不知道����,但是,他心里裝的是集體��,這是全村人公認的���。
記得有一年����,隊里殺了一頭豬�,我婆分了七兩肉,大年三十的年飯�����,我婆炒了一盤子豬肉粉條,端上桌子時���,還專門把這盤菜朝我父親跟前一挪再挪����,就算過了個年?���?�!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��,國家窮�,老百姓更窮。那個年頭����,有點點肉吃,都感謝肖爺爺喂豬喂得好�。
難忘之四:露宿公路兩邊
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,我村人也是緊緊張張了一陣子��。特別是到了晚上,大人們胳肢窩夾張能鋪得渾渾爛爛的東西��,領著娃們睡在公路兩邊����,害怕晚上睡在屋里不安全。天亮了鋪蓋一卷�,該干啥還干啥,又跟沒事一樣了��。一般是母親們帶著孩子����,一家挨一家,不分你我���。家長們三個一堆五個一群�,卷著旱煙����,有一哈么一哈地抽著,聊得最多的是年景收成?,F(xiàn)在回想起來,當時大人們怕不怕不曉得�,反正娃們無憂無慮��,嬉戲打鬧依舊���。有點兒“初生牛犢不怕虎”或者是“無知就無畏”哦。
此刻����,好享受那時的人有多么的淡定與從容!沒有喧囂����,沒有誠惶誠恐,這也許是一種力量���,是一種勇敢不怕困難的可貴精神�!
難忘之五:連陰雨的日子里
每年秋季的連陰雨是個熬煎�。一連半個月的雨�,就能聽到遠遠近近的“嗵……嗵……嗵……”的倒塌聲,沉悶而有力�。旋即就聽見了人的嘈雜聲,張家的后院墻倒了……王家的廚房塌了……劉家的茅廁墻倒了……大人們把娃關在屋里�����,怕的是出去不安全。連陰雨的日子��,上學的娃娃們也不好過����。沒有雨鞋,更沒有雨傘��,一張油布�����、一張塑料紙����,或者是一個麻袋,身上一披���,顧了前顧不了后���,顧了頭就顧不了腳,但是書包是必須顧好的�。那時的土路,可能談不上路基,雨天就更難行了�����!深一腳淺一腳地陷進泥窩窩子就拔不出來了��。那時候大人們不送娃上學��,特別是小女娃��,往往是邊哭邊走�,現(xiàn)在想起來,那時候的娃娃們挺可憐的哦���,自己也是其中一個���。如今的小孩,真的是無法體驗他們的祖輩父輩們童年時代的心路歷程��。
難忘之六:我外婆和我婆
外婆有一手好針線����。外婆自己養(yǎng)春蠶��,自己繅絲��,自己染絲線,各種顏色的絲線在外婆手里����,變成了娃娃身上端午香包、腳上的小花鞋��、嫁女嫁妝的繡品����。我記憶最深刻的是我外婆家枕頭都是自己種棉花紡線織布做成的,而且枕頭兩頭都是繡花檔頭�����,有各種各樣的花草����、有形象逼真的蟲魚,惟妙惟肖?���,F(xiàn)在回想起來,顏色搭配養(yǎng)眼更養(yǎng)心?��?��!
外婆還有一手好茶飯�����。蒸煮煎炒炸樣樣難不倒她老人家�,特別是外婆打的攪團����,光溜溜沒有疙瘩,漏的面魚長而勻溜����,涼在大茶盤子里或案板上的攪團不薄不厚,切成不長不短����、不寬不窄的條,油鹽醬醋辣子蒜末�,就那么一拌,開吃�����,色香味俱全�����,香到不可言喻啦�。
我欣賞我的外婆,因為她很會料理過日子����,外婆家的日子是那個時代最能體現(xiàn)“自給自足”內涵的。外婆離開我們十五六年了�,她整整活了一個世紀,溘然長逝����,真的是油枯燈干狀態(tài),這也許是我外婆的造化吧���。
我婆的“三寸金蓮”特別標準:三折��、一個大腳趾����、腳底到腳腕子處足有四寸吧�,是一個舊社會過來的小腳婦女���。我婆的茶飯手藝可以說是“一白遮百丑”,她的手搟面堪稱極佳���!毫不夸張地說����,那真稱得上是“粗細均勻�����、筋道可口���、觀感宜人”����。從我記事起���,我父親每次回家�,我婆都要搟一頓撈面����,而且第一碗就是給我父親的�!我婆總是給我父親把面調好端到跟前�,我父親接住碗就大口大口吃起來,真是“媽媽的味道”?����?��!
我婆有一副菩薩心腸,從不罵人����,就連三歲小孩的調皮搗蛋都不說一句,總是一句湖北腔“小娃子哦”���。我婆還有個“月下老”本事���,凡是經她牽針引線的,十有八九都成啦���,況且還不吃人家的酒席����,因為她“忌口”,不動葷腥����,就連蔥韭蒜都不吃,她說“怕熏了佛祖”�!也從不收人家答謝禮,哪怕是一瓶橘子罐頭�、一包麻餅。我婆不識字����,就連錢都認不得。有一年初冬傍晚��,已經明顯有了寒冷的味道����,有一隊賣瓷碗瓷甕的耀縣人路過我村,一共是十一個人����,人困馬乏,讓我婆給他們燒兩鍋開水��,就給七毛錢���,我婆爽快地答應了�。那時候燒的是玉米稈、麥草����,尺八鍋、兩鍋水��,整整燒了快兩個小時�。那幾個人爭先恐后給自己壺里灌水��,有的拿出大老碗用滾燙的開水泡冷蒸饃吃���,他們聊著輕松愉快的話題����,看樣子這一趟把錢掙了���!夜里十點多了他們才動身繼續(xù)趕路了��。一個像個領頭的人給了我婆兩張紙票子�����,說是一張2毛�、一張5毛,一共7毛�。第二天我婆讓我看人家給的錢對不對,我說是3毛��。頓時���,我婆傻了眼�,“啥�?7毛么,咋是3毛哩�?”我婆再沒說啥,只是自言自語道“唉��,這些人是耀縣的出門下苦人么”���。
我婆是個快樂陽光老人�����。雖說苦日子����、窮日子過了一輩子,可她總是那么愛串門�,東家坐坐、西家遛遛���,有時候在太陽坡里一邊補著爛衣服��,一邊曬著暖暖��。我婆一輩子都舍不得穿新衣服��,一年到頭除了走幾家老親戚時���,換上干凈的半新不舊的衣服��,幾乎全是補丁摞補丁的舊衣裳���,甚至還是絮絮絡絡的破衣服����。我婆不是沒有好衣服�,而是她習慣了。我婆自己壓根舍不得吃啥,只要有一口飽飯就滿足了��。像紅白糖呀�����、奶粉呀�����,大多都是我三爸給買的�,可她自己就是不舍得吃。她時常悄悄地用手帕包一包白糖或紅糖�����,揣在大襟衣服懷里����,不讓人看見,偷空給她的幾個好鄰居老太太送去��,其中就有周老太�、賈老太、寇老太���。每次三爸回來看望她��,總給我婆十數八塊零花錢����,而且都是換成了一塊一塊的,我婆幾乎就不花錢���,我到現(xiàn)在都不知道她把那些錢咋花了��。我婆臨終的時候��,她的柜子里“秦俑”奶粉成十袋子��、春夏秋冬新衣服多件����、紅白糖幾包子……多么節(jié)儉的老人?��。?/p>
說句心里話���,那個時候����,我愛我婆勝過愛我的母親。我愛我婆的慈母心腸��,愛我婆的善良熱心腸��,愛我婆快樂“湖拉?�!?���,我愛我婆的從不埋怨。
后記:我的祖籍是湖北鄖陽府�����,祖輩逃難到此����,安營扎寨,繁衍生息�。《陜西省涇陽縣地名志》中是這樣記述的:清中葉��,雒姓人由今本縣龍泉鄉(xiāng)雒家堡遷此建村定居時��,為祭祖先與故里人相爭,撕得祖像一角供奉�����,故取名角雒村��。
后來�,撤鄉(xiāng)并鎮(zhèn),對原來的自然村也進行了合并��,角雒村成了三渠鎮(zhèn)三渠村的角雒組�。這,就是我的家鄉(xiāng)����。
作者簡介
王楠 , 退休干部,熱愛文化�����。
責任編輯:王順利/《新西部》雜志·新西部網